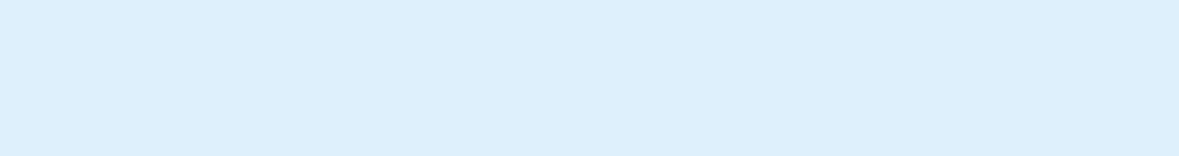对汪曾祺先生的作品是早有耳闻的,听说他写“人间草木”,写“昆明的雨”,写“生活是很好玩的”。如今掀开书页,近百年前的草木仍在阳光下熠熠滋荣,近百年前昆明降下的雨仍氤氲着柔软而湿润的雾气,倒悬在昆明一户小院门前的仙人掌顶头仍擎着懒懒的红色的花,过桥米线金黄的汤头上面仍浮着翠绿的葱碎。江南的白兰花开了,有卖花姑娘清亮而温柔的叫卖声,在石板铺成的小巷里慢慢地走远了。我踏着书页前行,也踏着柔柔的光阴前行,百年的时光流转并没有改变什么:没有改变花,没有改变雨,没有改变生活,没有改变人间清欢的至味。
古代文人喜在居室里悬山水画,忙里偷闲之时则停笔舒腕,静静地凝视画中的山川舒展、云蒸霞蔚,称之为“卧游”。在书桌上摆一本汪曾祺先生的书,闲暇之时静静读几页,繁忙之时抽空翻两下,也有“卧游”之感。汪曾祺先生一生所到之处甚多,五湖四海、大江南北,他几乎都记有见闻,但要说起他一生痴绝处,总得是昆明。抗战之时,他为求学奔至昆明,就读于西南联大。国破山河的时候,物资紧缺、生活匮乏,一天天似乎都有绝望的影子笼罩在头顶上,他却能在最暗淡、最绝望的现实的角落里,慢慢地品咂出生活的一点甜味来。他在翠湖看鱼,泡茶馆,看满眼热热烈烈的花在西南中国开得繁茂;在书店里流连,从书架的最顶层意外地寻到自己渴慕许久的书籍便像寻到宝藏一般如获至宝,兴高采烈;从一条勉强开了许多铺子的商业街走过,嗅着气味品评咖啡和红肠的好坏;和同学出游,在微雨的天气被困在饭店里,也不急不恼,慢慢地喝一盅茶,看微暗的天色下细细密密的雨点把店后面茂盛的植物淋得润泽而光亮,听几只店家养的老母鸡发出轻轻的含混不清的啼鸣;在茶馆喝茶时凑过去读墙壁上的涂写,从里面整理出许多不知何人、何时、何心境所写的诗。读汪曾祺先生的书,便仿佛置身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昆明;虽然从未踏入、也再不可能踏入时间洪流中这座小小的城市,却已经对她生出了故乡般的眷恋。或许正是因为汪曾祺先生,昆明在我的记忆里似乎总是湿淋淋的:湿润的白雾弥漫在山间,青石板铺成的小径被水洗得洁净而亮堂,路边的草绿得逼人的眼,花在暮色中沉沉地低下头去。有一个人在绵绵的雨丝里不撑伞也不快步,仿佛习惯了昆明的细雨和这座城市一般,走到一处不起眼的旧院子前,轻轻叩响了门扉。
汪曾祺先生是个对吃很有研究的人。虽然可能还不及梁实秋先生专门作《雅舍谈吃》一书,但散文中常散见他对吃的关注和理解。他会专门写一篇小散文,事无巨细地记载家乡能吃到的小鱼,是极便宜的食物、极平淡的叙述和极克制的情感,读罢却觉到绵绵乡愁,像昆明轻轻地雨丝一样铺天盖地地卷来,虽不至于淋湿衣衫,可也已经足够唤起闲愁。吃也是他对昆明的记载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他记喝一口会烫掉舌头的过桥米线,记咬一口就会溅出汤汁的包子,记骨酥肉烂的汽锅鸡,记用马肉制成、大油煎制的血肠,记昆明数不清的鲜美的菌子。连文革期间被发配改造,要求他画马铃薯图集时,他都要把剖开画好的马铃薯埋在炭火里烤着吃,甚至有些得意地宣布“我是全中国吃过最多种马铃薯的人”。关于汪曾祺所写的“吃”,最出名的莫过于《高邮的鸭蛋》一文了,甚至被选入中小学语文教科书。高邮金黄的鸭蛋也由此从汪曾祺先生一个人的眷恋和乡愁,变成了全国许多人铭刻在童年、久久不能忘怀的一份好奇和向往。时到如今向人提问,语文教科书里那样东西让你印象最深,觉得最好吃,对面的人十有八九还是会回答:“高邮的鸭蛋啊!”
汪曾祺先生曾言:“生活是很好玩的。”那么,生活怎么才能好玩呢?汪曾祺先生在《苦瓜是瓜吗?》一文中已经给出了回答:口味要杂一些。在这篇散文中,他虽然是针对文学创作和批评给出的意见,但这充满哲理的建议也适用于生活本身。要过好玩的生活,就不能先给生活预设好框架;好玩的生活,必定是丰富的生活,生机勃勃的生活,必定不是固步自封的生活,死气沉沉的生活。奇怪的、过去没有尝试过的食物,不妨尝一下,而不是立刻皱紧眉头说“不吃不吃”,就算味道不合口味,也算是好玩了;新鲜的、过去没有尝试过的事情,不妨试一下,而不是还没有开始就告诉自己“我没做过,这个不行”,甚至警惕地问“这件事有意思吗?有意义吗?”,去攻击与自己选择不同,去做这件事的人。眼睛要尖一些,发现生活中细碎的乐趣;口味要杂一些,在新鲜事物面前不要一味警惕;心情要快乐一些,如此,生活才是很好玩的,如此慢煮生活,才能品味出潇洒自在、幸福满足的人生至味。
汪曾祺先生《慢煮生活》一书,真如同一碗浓会了生活百味,精心烹制而成的热汤,其中有草木、饮食、光阴、历史等诸多佐料,却汇成同一种幸福、满足、优雅、快乐的生活之味。请你也挑选一段时间吧,不一定要是阳光融融的午后,也可以是结束了一天工作的疲惫的夜晚,或者是赶往工作岗位时忙碌的清晨,翻开这本书,让一碗暖融融的生活之汤,点亮你对生活的勇气和热爱,告诉你“生活是很好玩的”,告诉你“人间有味是清欢”。
(中铁房地产集团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孟淼)